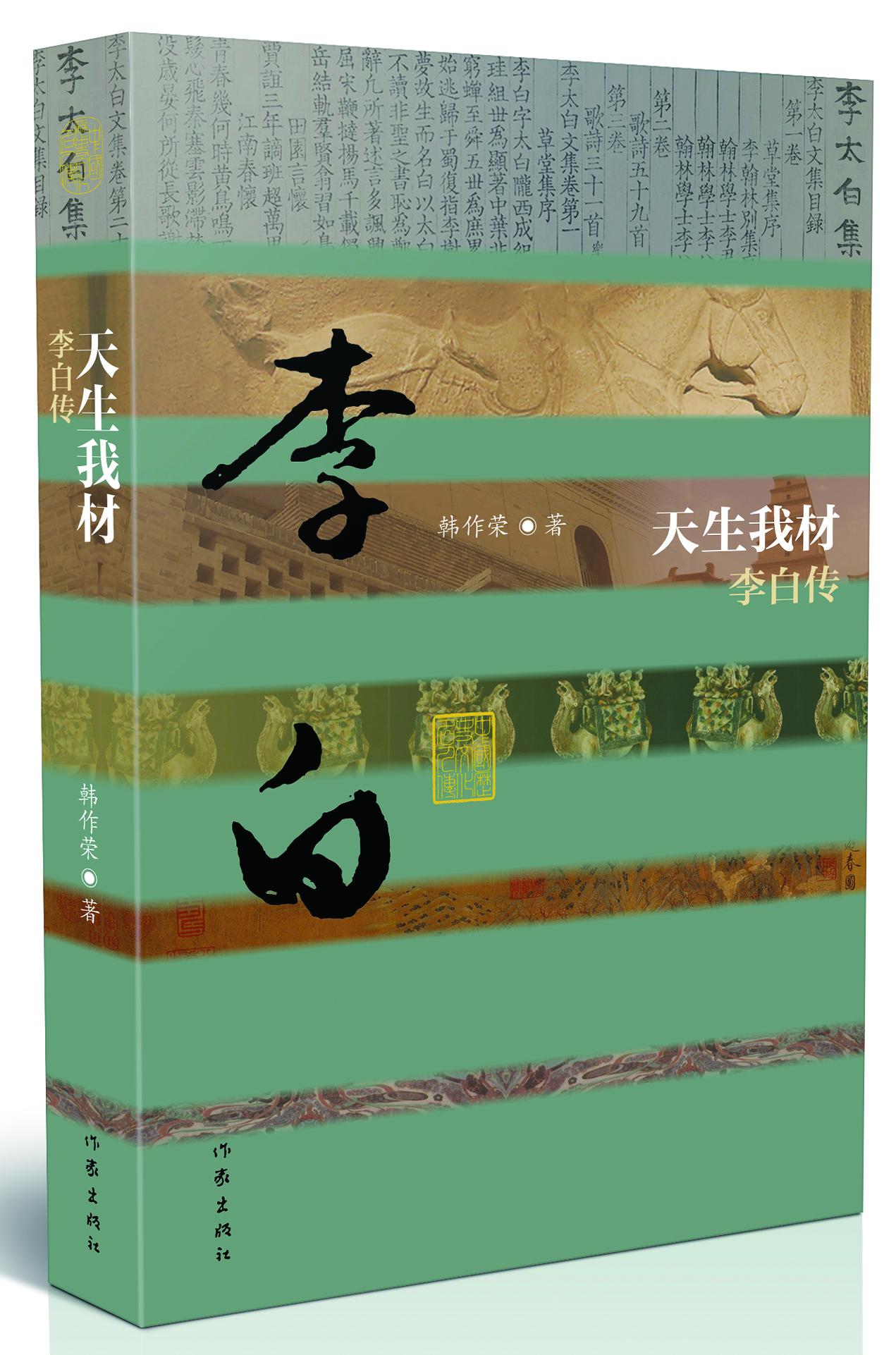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一种,韩作荣先生的这本《天生我材:李白传》却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 韩作荣先生于2013年11月12日凌晨辞世,于不幸和悲恸中万幸的是一本30余万字的“李白传”书稿刚刚在去世前改定、完成。韩作荣先生从2012年3月开始用了8个月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研读资料,2012年10月13日开始动笔,一直到2013年10月7日陆续草成。2013年11月3日改毕,9天后离世……
《人民文学》2014年第3期选发了《李白传》遗稿中的部分章节,卷首尤其强调“本刊以‘特稿’发出韩作荣的《李白传》,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与怀念,更重要的是,这部传记本事扎实,言外滋味丰盛,值得收藏,适合精读细想”。
这是一部遗著,也是一份手稿,由韩作荣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稿纸上。这种手写体的劳作方式在这个电子化写作和临屏阅读的时代几乎绝迹。尤其写作《李白传》更是一个耗日持久的巨大工程,关于李白的研究资料已经难以尽数,而这些资料的搜集、抄录以及书稿的伏案撰写,已经对一个人的体力、精力、耐力都是巨大的考验了。韩作荣先生的辞世也与其几年来为写作这本李白传记所累积的压力和超负荷身体运转有关。
一个诗人辞世,一本诗人传记得以诞生。
为李白做传绝非易事,而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李白不只是被“经典化”“神化”甚至已经“神仙化”了,但这又是特别值得予以尝试的诗学工程。
一个伟大的诗人需要的是伟大的“读者”。尤其是从“诗人”身份写作李白传记的角度来看,韩作荣这本《李白传》在同类文本中具有补白的性质,结构完备、面貌突出而精彩纷呈。众所周知,韩作荣是当代著名诗人,由诗人为诗人作传更具有敏感、会意的精神共通性以及灵魂的天然亲切感以及自洽性,也就易于打通时空距离的隔断,从而为深入面对另一个诗人的精神世界、诗歌世界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了诸多便利、可能性以及效力,“一个写诗的人或许更能理解诗人的心态、性格,更易为其豪气及其一生的悲剧所感染,体味其天成的神来之笔的可遇而不可求”。
2. 之所以说为李白作传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除了要通读、理解、消化、比较、整合、考辨几乎所有关于李白的诗歌、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这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历来就缺乏“传记”的传统,比如李白只是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才子传》《唐才子传校笺》中被极为简略地提及且相互之间诸多矛盾和穿凿附会之处,至于后来的笔记小说就更不足为信了。往往一个诗人“传记”资料本身是缺失的,而更多是通过诗歌承担了记忆和记录的功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有诗为证”。然而就唐诗而言,在其近300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诗歌传统、诗人形象以及抒写方式上恰恰普遍呈现出“传”和“本事”的整体缺失状况。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所涉及到的诸多诗人的生平、情感、遭际以及流徙等等多为碎片化的,其间有很多的空白和盲点,甚至具体到一首诗的系年和真伪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比较极端的情况是龚自珍认为现存的李白诗歌只有120多首是“真品”。
为一个“诗人”立传,“诗”和“人”是不可二分的。质言之,除了要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的特质、风格有着极其深入的全面了解之外,还要对生平家世、品性癖好、交游、远游、政治经历、人生轨迹等等进行谱系学和年表意义上的“本事”予以完备的搜集、考证、勘察和寻踪,甚至要进行重新的发掘以及知识考古学的工作。
对于一个社会阅历丰富且广泛出游的诗人而言,韩作荣在此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李白一生所走过的地方,其祖籍故乡、长居短居之处,我几乎都去过,可他‘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安陆,却从未涉足。或许是欲写这部《李白传》的缘故,读太白诗中言及的行踪,一入眼帘我便想起那里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人情冷暖、人文地理,写起来感到心里有底,似有一种实在感无形中托着,心手不虚。可从未领略其风貌之处,看资料时也感到云里雾里一般,不敢下笔。”
尽管时过境迁甚至沧海桑田,但是有时候实地考察往往会获得更为真切的历史现场感,而感同身受是最具温度和可信度的对话方式,“晚居于白兆山宾馆。因这个季节已无游人,空山更空,山居清冷,阴凉之气逼人。接待者看我是一位老同志,特给我安排了一个大房间。可空调小,房间大,虽整夜开着暖气,房间仍无暖意,冷风从窗缝钻进来,盖了两床被子仍冷得哆嗦。这时节我想起李白在这山间一住多年,这冰冷的冬日该也难耐”。甚至于当年的废墟、遗迹以及行踪的山川水流间能听到当年诗人的呼吸。对于当年李白的行迹,韩作荣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证甚至实地考察,比如早年李白在蜀地壮游的时候韩作荣就从具体的空间、路线和坐标予以了极其精确的还原,比如李白去江油关“必走通陕、甘的艰险蜀道阴平道。此小道为三国时邓艾伐蜀时于无人烟处开辟的山势凶险、布满荆棘的小路,其时邓艾率兵将行荒无人烟地七百里,于险恶处‘滚毡坠石’而下,奔袭至古江油关。”
3. 尽管对于唐代诗人而言“诗歌”具有传记功能和文学史因素,但是由于李白的“诗”与“史”之间往往呈现了虚化和模糊的陈述关系以及李白形象大体是通过诗歌中的“角色扮演”和特定的话语角色而强化和塑造出来的,同时也出于对唐诗传统的深入理解,最终韩作荣不得不选取了“以诗入史”的方式。即沿着李白诗歌的生成脉络来索解、追踪和叙写李白的生平,而这是最为合宜而准确的方式,“李白飘忽的行踪、起居故事、所思所想、平生经历等,史书鲜有记载,然而诗人所历之处,多有品题,虽动乱之时,其作品十丧其九,但其所留千来首诗书赋文字,仍如日记一般,透露出一个鲜活可感、有血有肉、才华横溢、盛气凌人、个性鲜明的李白来。”
“以诗入史”,就必须对“诗”有着独特而精准的把握和理解,继而再考察“诗”与“人”“时”“事”“史”的互文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具体到唐诗传统以及李白写作显得空前复杂而含混。
单从李白诗歌的题材来看就相当广泛、多样,比如寻仙问道、山川风物、离愁别绪、边塞远征、民间疾苦、社会万象、怀古幽思等等,显然,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和“道教诗人”“隐逸诗人”的简单化标签所能涵括得了的。
长久以来在阅读效果史中李白成为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豪放诗人”“乐观诗人”,但这显然是将李白诗歌文本的风格直接对应于诗人人格的刻板做法,而作为个体的人以及诗人的复杂性显然由此受到了遮蔽。韩作荣对宽泛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持审慎和疑问的态度,“对李白最常见、似乎已成为常识的说法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对于李白式的“浪漫”韩作荣将其中一个原因归结为“魏晋情结”,而李白对“魏晋风度”的追附就自然离不开酒,离不开他一贯的宿醉以及鲸饮、豪饮和狂饮,“我相信李白喜饮酒该是受家族源自西域粗豪之风的影响,也与蜀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之及时行乐的风气有关”,“或许,李白喜欢酒,更多的缘由是他深受魏晋情结,即纵酒携妓的名士风流的影响有关”。而只有真正地通读和深入理解李白的诗文,才能真正去除那些“惯见”的迷雾和刻板印象制造的“诗人面具”,还原出一个诗人的生命本相和诗歌的真正质素所在。比如针对着一般读者对李白的“豪放”“旷达”“狂放”的浅层印象和误解,韩作荣予以了有力的提请和拨正:“读李白全集,读得越多,越发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由于李白思想观念的多元性,便注定了他心态的复杂;由于他理想、抱负颇为高远,其破灭失落时刻则摔得越疼、越惨痛;他的一生郁郁不得志,当一个过于张扬膨胀的自我处处碰壁,如气球胀破而粉碎,只能成为人生的悲剧。在这种情境之下,失意、愁苦、惆怅、哀怨、悲怆则如影随形,伴随了他的一生”。
4. 李白的诗歌充分展现了一个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精神意志以及天马行空、电光石火般的怪诞驰骋的想象力。这是一个近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诗人,相关学者统计过李白诗歌中极高密度的700多次的第一人称“我”“吾”“余”,“李白关注的焦点始终有‘我’,一生立身行事的出发点总在‘自我’,其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都在‘我’这个支点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志向的言说,遭遇的感受,抑或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甚至写神仙幻境,亦是‘我’的独特感受,是理想的外化,是主观感受的真实,情感逻辑的真实。”
这一诗歌中的“自我”显然既是性格、人性以及精神和世界观层面的,也是与现实、时代、历史甚至政治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对文本化的“自我”予以客观和准确的认知,“他是一个以高度自我为中心的诗人,主观色彩异常浓厚。诗作为一种主观的创造自然不能没有自我,即使展示一个时代也是诗人自我表达的主观感受,诗人以自我的体验和洞悟折射时代精神,体现诗人对人生、自然、社会的认知、判断和理解,继而形成一种创造。”
李白正是通过流传下来的不到1100首诗歌塑造了率真、狂放、怪诞、豪侠、放任不羁的疯狂行为和独特鲜明的个性,也由此塑造出了游侠、求仙问道者、狂饮者、求仙者、狎妓者、笑傲权贵者、“诗仙”、“谪仙人”的天才诗人形象。然而,诗中的“李白”显然是修辞化的,其与现实中的“李白”显然是具有差异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李白”恰恰是通过“诗歌”中的人物、意象、场景、情绪以及背景空间来完成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诗歌的时间、事件背景却缺乏必要的交代,而往往是虚化的、模糊的、不连贯的,甚至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又增加了歧义和误解的成分,“诗人用语常不以常规,匡山不说匡山,而称岷山之阳,让后来者生出疑惑,并生误解。”
比如李白在诗中自言于维扬(扬州)时曾“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而很多研究者包括海外汉学家就认为这是李白为制造自己的侈夸逾常、豪迈慷慨的“诗人形象”而有意夸大为之,韩作荣则在此评价意见的基础之上再进了一步,“我也认为太白有夸大吹嘘之嫌,可‘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却也太合太白之性格。太白‘少任侠,不事产业’,任侠仗义,结交甚广,扶危济困,为人排忧解难,对朋友解囊相助,而金钱非自己挣来,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乃至于后来自己捉襟见肘,生存艰难,也是实情。”
甚至从地方性知识和属地性格来看,李白任意怪诞的行为与当年的司马相如、扬雄和陈子昂一样都带有典型的“蜀人性格”。
由此,从传记学来说这里就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作传者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完成深度“还原”的工作。
5. 从《李白传》来看,韩作荣不只是从“诗人”的角度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歌特质和精神世界,而且还更为重要而真切地予以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还原。而这至为关键,这是祛除了“神化”面具而还原出真纯的人和诗人面孔的本真时刻,“我是将太白从仙还原为人来看待的,纵然他是诗人、奇人、狂人,才气横溢、名传千古”。
主体性和心理时间视角下的人,是具有特异性格、人格、心理和独立意志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个体,对于李白这样多侧面的天才诗人和异端诗人来说更需要对其性格、人格心理以及人性弱点等予以具体化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剖示,“如太白,却是永远长不大的人,他的心理年龄仍旧年轻,并葆有天真,仍活在梦境之中。说其是哲人和孩子的混合体,于独有的孤傲自负的性格中仍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为了还原李白的“人”以及“人性”,韩作荣甚至会在行文中偶来极具诗人特质的“闲散笔调”,有时从生活现场和日常饮食来理解当年的李白,“我惊异于扬州菜的清淡但多味。不知道初次到扬州的李白吃没吃过扬州炒饭,用芦管吸吮的包满鲜美汤汁的大包子,那细嫩的干丝,以及将素白的水豆腐切得如发丝一般精细的羹汤,和经长时间于罐内文火煨烤却极入味烂熟的猪脸之类,这些极好的菜蔬,该是太白的下酒之物。而这些食物的制作大都颇费工夫,所谓慢工出细活,没有耐心,没有闲情逸致以及安逸享受的时间和心志,以及熟能生巧的技艺制作和享用皆不可能。”显然,这样的“闲笔”和“散淡”化的叙述方式的穿插就避开了一般传记因为过于谨严、周密、逻辑和大量引用原文而带来的阅读的紧张感和疲累感,而是带来了缝隙和孔洞。
6. 《李白传》是一部诗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备的著作。我们对一部传记作品还有一个要求,这就是“真”“真实感”以及“求真意志”。尽管任何传记都带有修辞化以及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形成的“传说”“传奇”“故事”“民间野史”就具有了合理性。传记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史传中的史实,而是语言化和精神化的“现实”。质言之,传记视界中的历史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即使传主是同一个人,但是传记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角度却因人而异。
传记的“历史功能”是以“真”为前提的,这就要求做传者或传记家具备个体主体性、求真精神能力以及重新组合历史的能力。而韩作荣的《李白传》不仅阅读、比较和整合了大量的关于李白的“自述”、同时代人的“旁证”以及后世的相关研究材料,而且还要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和矛盾之处进行审慎甄别,“我搜集那些论证有据、言之成理的可信的史料,辨析众说纷纭的家族史、出生地、故乡、生卒年月等莫衷一是的言说,从诗文中查其行踪、心理,从其自述中洞悉生平籍贯、生存状态与气概、心灵。尊重有共识的看法,去伪存真,力争探究出一个真实可信、还其本来面目的李白来。”
与此同时,韩作荣在最大化的可能性空间通过诗、人、事、史这四者立体化的对话实践还原出了一个尽可能真实而复杂的李白。韩作荣不断强化了对李白的重新解读和理解,剥除了那些惯见和面具,通过诗人的“当代眼光”“人性视角”与李白和唐诗以及传统进行深入的对话、磋商与沟通。
任何一个诗人和作家都有深深的对抗时间的焦虑,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穿越自己的时代而抵达未来的读者。而这样的诗人具有总体性以及精神共时体的特征,他们用诗歌对抗或化解现实境遇中的焦虑、茫然以及死亡的恐惧,从而借助文字世界得以永生。李白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而从“理想读者”的角度来看韩作荣先生的这本《天生我材:李白传》也具有面向“未来读者”的质素和可能性。